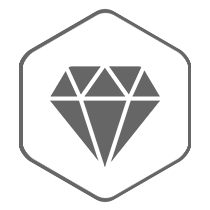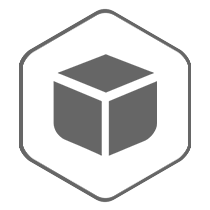吃过晚饭了,可以详细说说上午我发的那条广播:有谁租住过北京的那种人防工程地下室?
一、
如果不是有些契机,很多人啊,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一辈子都在替别人为自己掘墓。
考虑到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人防工程“,先简单说一下:人防工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深挖洞,广积粮”,一些大城市为了防止被轰炸,在市区里修建的一些地下室工程,这些地下室特别像地道战的地道而不是今天写字楼的停车场,有一个一个的许多房间,有公共卫生设备等等。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一些新修建的居民楼还是会修建人防工程,政府现在还有人防办公室。
后来,北京的这些人防工程基本都被改建了,有些改成了廉价旅馆,有些改成了居民活动中心,毫无疑问,肯定以前者为多。
2004年初,我大三的寒假。因为学校要求,我跑来北京某党报实习1个月,托报社的一个姐姐帮我租房子,也不知道是那个时候租房市场不像今天这么发达,还是姐姐太忙没有仔细找,她告诉我,因为我只住1个月,又要离报社近,只找到了一处地下室,条件很糟糕。我父母一听,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让我吃苦的机会,颇为高兴的答应了。
那天,我跟着姐姐来到了红庙一个居民楼门口。居民楼前的马路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工地,看不出要建的是什么建筑,但工地宽大的简易围墙上写着”新光天地“,这四个字我是印象深刻的。
走过地下室长长的幽暗的通道,到了下面突然灯火通明起来,这里的床位一天只要8元钱,便宜的不可思议。我拖着行李到了房间,除了潮湿,并没有发霉的味道。事实上,人防工程不同于一般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很好。
看到这个房间,有那么一霎那,我居然觉得很开心。
小时候读童话,特别向往那些住在地下的小动物,土拨鼠,田鼠,鼹鼠,野兔……它们会在冬季漫天飞雪的严寒里,宁静、舒适、温暖的住在自己地下的小窝里。它们会建造许多房间,有的贮藏坚果,有的铺上干燥的稻草,它们可以足不出户躲过整整一个冬天,把皮毛保养的光滑柔顺。
这样的地下家园,会让童年的我感到格外有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的想象很快就被卫生间粗大的水管下滴滴答答的滴水,地上和尿液混在一起的积水,以及那个看上去很不友好的室友所击碎。
但我还是住下了,别无选择。
二、
后来的日子,可以只讲三件事。
就先从我这位室友讲起吧。他比我大一岁,当时是蚌埠一所高中的美术生,已经在北京呆了好几年,年年考美院,年年落榜,那时候他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那谁谁画的跟shi一样“,但我从没看见过他的作品。与他外表那种不良少年的面庞不同,他为人蛮实在,我们很快成了卧谈时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总是开玩笑的说”你们大学生都是垃圾“,我也会说,没错啊,都是垃圾。
那段时间我正在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胡兰成就是那年流行起来的。他看我看得津津有味,拿起来翻了翻,说,”这人干嘛的?“我说,”民国的一个作家,张爱玲的前夫。“见他貌似有兴趣,我又说,”他经历可丰富了,还跟着汪精卫干过,后来去了日本……“我话还没说完,小伙子警惕的看了我一眼,说,”是个汉奸?“
我说,”是呀。“
他的手像过了电一样,马上把书扔到我床上,非常鄙夷的看着我说,”汉奸的书你也看,脏了我的手。“
我当时也很惊讶,我似乎理解了他说的”大学生都是垃圾“,包含了什么样的意思。
用今天的观点看,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粉红“,爱国爱得动物凶猛。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是因为”地命海心“之类,他对国家、权力、社会等都没有什么哲学思考。只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需要一个立场,需要一个归属。对于读书思考都不多,社会经验有限的他来说,国家,是手到拈来、既朴素又容易升华的最好归属。
我并不反对爱国,但爱国和爱生活一样,是需要思考、审视才能判断的,并不是什么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当然,很多人终其一生的自我归属,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国者。
三、
在报社实习的日子很舒服,我每天在地下室睡到十点,因为地下室不开灯就是黑夜,所以睡眠质量很好。醒来后去报社吃午饭。工作上,领导对我很好,老记者对我也很好。因为是党报,我的大多数工作就是去政府部门或是国企,拿到通稿和一些小礼物,如果是去网易搜狐这种地方,还能美美吃一顿,甚至觥筹交错,回来把小礼物分一分,把稿子一发就好了。
我每天坐公交车去报社,有一天,和我在车站等车的正好是新光天地的建筑民工们。车来了,他们横冲直撞,大呼小叫,推搡着我上了车。我的相机都差点被撞到公交车里的栏杆上,我感到非常恼怒又无奈,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窗外工地上“新光天地”四个大字晃到了我的眼睛,我忽然想到,我,一个住地下室的本科生,和这些民工们有甚么本质区别?就因为学历?还是因为我从事的是室内的文字工作?还是因为我躲在一个党报里虽然我现在还只是实习生?……
想提醒一下大家,在2004年,HU先生“垂拱而治”的十年刚刚开始(这也是后发判断了),第一届(1999级)扩招的大学生才刚开始毕业,公务员考试常常报名还报不满,社会上也没有诸如“搬砖”、“IT民工”、“金融民工”这些自我嘲讽的词汇和现象。那年头,土著博士毕业进985还很容易,“白领”、“小资”这些身份还闪闪发光。那时候还没有豆瓣,那时候《南方周末》如日中天,那时候我的人生偶像和职业偶像是《经济观察报》副刊一位名叫符郁的师姐,那时候……
扯远了,扯回来。总之,早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一个985大学的本科生,本质上和民工没有区别,都是“劳工阶级”,以后都要靠工资养活自己。这种意识在那时绝对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焦躁与不安。
四、
我在报社跑的是经济新闻,除了上面说的与政府国企打交道外,也干过一些别的好玩的事情。比如,曾经和西城区工商局一起端过一个卖窃听器的小公司,我还扮作买主去踩点,谎称老板娘要监听有小三的老板。但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跑楼市那几次。
2003年非典,北京房价停滞。2004年初,就有松动的迹象了。不过,那时候报社的老记者们都觉的北京房价涨到2008年奥运会就会到达峰值,奥运会结束就会跌。所以,我知道的买房子投资的人并不多。我要说的是有次跑楼市采访,遇到一位老北京,人和气的很,跟我瞎侃,有两个体会:第一,现在四环的房价都六千了,听说西城有的地方都快一万了,这房价以后怎么办啊?老百姓才挣几个钱?肯定到顶了。第二,我们家原来就在城里头,后来拆迁给拆到外头来的,我们家祖辈就住里头,怎么现在住在城外头那老远的地方了,当年也没多少拆迁款。
他这第一个体会,我就写在报道里了;这第二个体会我记在了脑子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就算是老北京,几代的土著,也会有被拆到城外还没多少拆迁款的境遇。事实上,在那短暂的一个月里,因为是正月期间,我曾跟着市民政局“慰问”过北京周边多个郊县,给五保户发米面油,真正见识到了首都原来还有不少很贫困的地方,第一次听见有些远郊北京人讲的方言,根本不是京腔,而更像是唐山话。
在很多立场、境遇、不可知的未来面前,地域——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居住时间——是拿暂住证的还是刚落下户口的,还是几代的土著,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五、
实习期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爸突然打电话说来北京出差。其实,我在地下室住的日子并不觉得多么艰苦,相反,我觉得很充实,我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所以一切都还算新鲜。唯一不方便的是地下室没有信号,我每天要在外面的麦当劳里坐到十点多才回去。可是,一听到我爸来了,我一秒钟都没耽误,装好行李就去宾馆找他了。
道理很简单啊,我虽然并不觉得地下室有多艰苦,但能住的舒服,我干嘛要住的不舒服呢?如果肉糜管够,人人当然都要食肉糜了,“何况我哉?”(此处语气请参考贾迎春)
那段实习经历的一些感触,在日后的十几年的生活始终鲜活,我觉得,“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分不开的,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自治的诉求;没有阶级意识,就没有和谁自治、何以自治的行动。都说中国像一只雄鸡,要我说,中国更像一只洋葱,每一层就是一个阶层。中间的那个芯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需要的时候就会剥掉最外面的一层,再有需要的时候就再剥掉最外面的一层。
广东的北面都是北方,洋葱芯儿的外面都是表层。
那些仅仅因为有个学历的、有个户口的,以及有点钱的、有一两套房子的、在本地居住了好几代的,甚至那些所谓“体制内”的,等等,在这个洋葱里,如果你不属于中间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芯,那么,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层呢?能不能算出来什么时候就剥到你这一层呢?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算不出的。如果都知道,算得出,那,中国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PS:大S老师说,我的样本不全,作为《保卫大S老师近卫军》的召集人,我拥护大S老师的判断。所以,我也希望有同样曾居住在地下室以及更差环境的朋友分享一下经历。
作者:danyboy(来自豆瓣)

 2019-07-22 13:31:33
2019-07-22 13: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