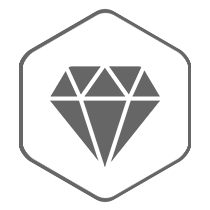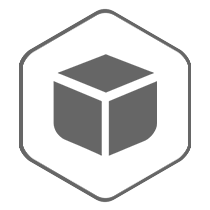国漫会崛起吗?如果站在《姜子牙》上映之后的时间线上,答案大概率会很悲观。在社交平台上,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的讨论呈现着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并随着“营销期”的过去在10下旬之后彻底走向负面的一端。
有人批评它叙事无力,无法驾驭宏大命题,概念设定混乱、人物设定缺乏特色,进而引述出“中国缺乏讲故事的人”这个观点。也有从业者进行了技术分析,指出《姜子牙》里视觉上的“暗”(被称为“关灯”)等细节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偷工减料”,进而证明了“专业对资本的服从”。

(知乎上最热的回答之一)
人们甚至已经开始对“国漫崛起”这个话题本身表现出了厌烦情绪。
在人们的记忆里,无论是2015年的《大圣归来》、2016年的《大鱼海棠》、2019年的《白蛇:缘起》、《魔童降世》,还是更早在《魁拔》、《十万个冷笑话》,几乎每部作品都承担过这句口号,吸引过人们的振臂一呼。可以说,在近十年的舆论讨论中,国漫似乎从来就没有缺乏过所谓的“希冀”。
而“总是希冀”,这显然太不正常了。
从起点到高光
“国漫总是崛而难起、复而不兴”是一种错觉吗?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如果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或者放大对于“国漫”的定义,似乎也可以找到这个论点的背后内在逻辑。
毕竟用“崛起”绑定“出道即巅峰的国漫”,确实太不合适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在万氏兄弟的主持下,近百名工作人员绘制了2万多张画稿,历时一年半做出了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铁扇公主》,影片不仅迅速收获票房,更是隔海影响着一位笔名“手冢治虫”的中学少年。在《手冢治虫物语 我的孙悟空》中曾记录过这一段回忆:
闯入电影放映室的手冢治虫和放映师看着海报,感慨 “万籁鸣导演真是了不起,日本如果能制作出这么高水准的电影就太好啦”。

(出自《手冢治虫物语 我的孙悟空》)
不过“手冢治虫”同学还是低估了孙悟空的魔力,万氏兄弟的巅峰才解放后才到来。
那是1957年,脱胎于东北电影制片厂卡通股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下称上美厂)正式成立,万籁鸣也在抗战结束后重归,担任制片导演。而原本因战事中断的《大闹天宫》也重新提上日程。
1959年冬天起,团队通过实景考察,从古建筑、壁画、泥塑造型等进行创作取材,几易剧本,反复打磨孙悟空形象。等到了绘制阶段,更是埋首作画两年,按照当时10分钟的动画需要画7000张到1万张原画进行推算,《大闹天宫》50分钟的上集和70分钟的下集,大概需要8万到12万的原画。
按照现在最流行的说法,这是当时连同美国动画产业内,标准的金字塔尖,其工艺水平稳稳碾压后来众多“幻灯片”式的本土动画片。而也正是这种金字塔尖式的存在,让国漫的第一波行业巅峰充满了“游刃有余”的味道,从题材到作画风格可谓天马行空。
这一时期,以上美厂为代表的中国国漫人先后制作出木偶动画《神笔》(1955)、剪纸动画《猪八戒吃西瓜》(1958)、折纸动画《聪明的鸭子》(1960)、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1960)等等融合传统民俗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动画作品,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即使在条件极为困难的1966年到1976年间,上美厂也制作出了18部作品。
今天,当人们回忆起国漫巅峰时,所感慨的民族特色、精工细作的印象,大概率来自在这个阶段,许多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也在这样的热潮中被国漫塑造成了“国民记忆”,定义了几代人的童年。
在《神笔》中,拥有神奇画笔的马良,落笔成真。这种奇幻的想象,丝毫不亚于十余年后出现的,那个拥有神奇口袋的哆啦A梦。而寓于故事中,神笔为穷苦百姓作画的设定,马良不为官员画金元宝的情节,更是将中国朴素的善恶观,播种在木偶动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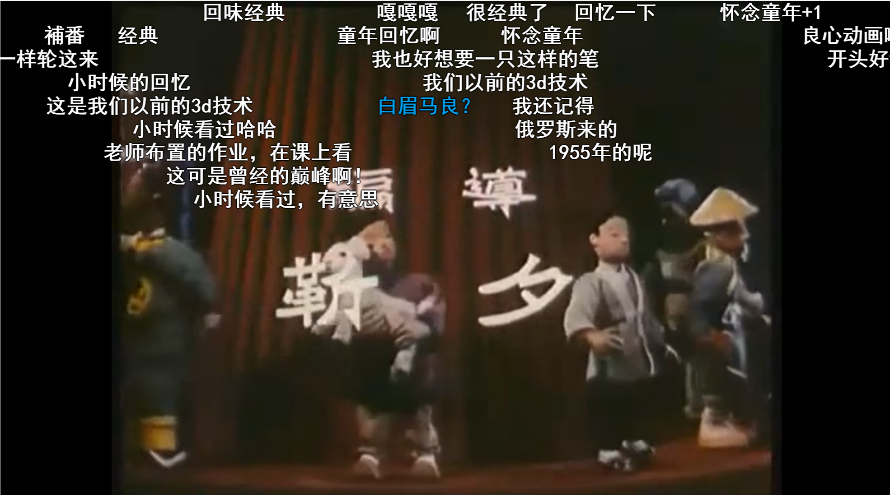
以《小蝌蚪找妈妈》为代表的水墨动画作品,将艺术极大程度融入动画生产。在那个年代,想要把水墨画作搬上银幕,不仅要做到手稿的还原和精细,更要确保同一个动作水墨色彩的相同和连贯,还需要想尽办法制作出渲染效果。因而当团队克服阻碍,将动画呈现在世界面前时,水墨动画惊艳了无数人。
日本动画大师高畑勋,就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直言,“特伟先生的水墨动画片,让我们惊叹不已。可以说,我们那些留白较多的作品正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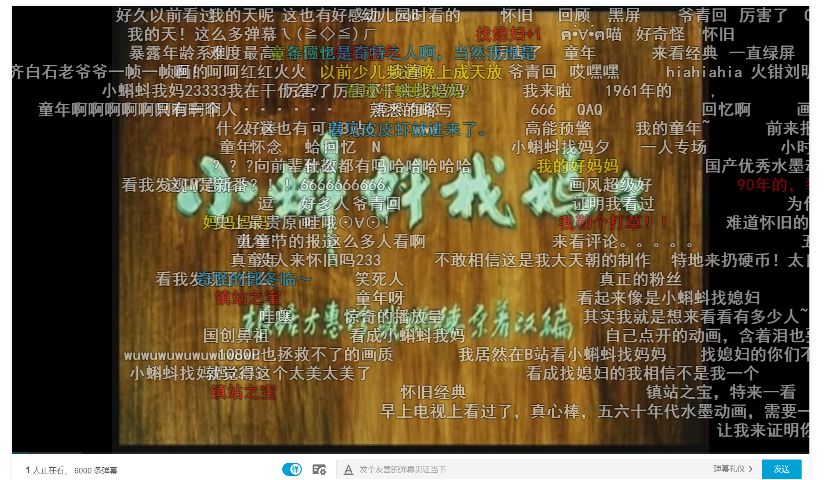
转折然后还是转折
国漫的下一次巅峰在哪里?很多人会把答案指向80年代。
当时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放,大量动画也伴随着各种工业产品的大发展走出国门。并且在专业层面也获得了极多认可。
比如1980年《哪吒闹海》成为第一部入选戛纳影展的华语动画片,1982年《三个和尚》获第32届(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短片竞赛最佳编剧)、《鹬蚌相争》获得1984年第34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银熊奖。《瞭望东方周刊》在此前报道中曾提到,在这一时期,上美厂共有24部影片在国际上获得37个奖项。

但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中国动画走向极致高光的时间节点上,危机也萌生在吹来的南风里。
80年代末,广州、深圳等城市陆续成立了一大批为国外厂商代加工的动画公司,所开出的薪酬是当时上美厂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时任厂长的周克勤曾惋惜道,自1986年至1989年,上美厂外流人才近百人。
伴随动画和动画设计的人才流失,上美厂不可避免的遭遇了创作人员结构断层,生产能力下降,经济滑坡。
而这个趋势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也无力阻挡的,甚至雪上加霜。伴随统购统销的取消,自产自销、自负盈亏,彻底被拉入市场化浪潮的上美厂不仅需要与拥有中央电视台发行和放映渠道的央视动画部竞争,更要与风靡中国的日本动漫竞争——
1980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引进《铁臂阿童木》黑白版,拉开大陆引进外国动画的序幕。此后20年间,日本动画走进中央及地方电视台,《哆啦A梦》、《圣斗士星矢》、《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等动画成为一代青少年的童年回忆。

面对竞争,长期代表着国漫生产力先进方向的上美厂,曾经做出过非常“堂堂正正的正面回应”,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倾全厂之力制作出《宝莲灯》和《我为歌狂》两部好评率极高的作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两部作品的情感越来越倾向于悲壮。
首先在成功的方面,《宝莲灯》率先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制作模式,采取先配音再根据配音效果进行动画设计,并且邀请姜文、宁静、徐帆、陈佩斯等一众明星参与动画录音,在“商业化运营+商业化制作”的双轨思路下最终票房达2900万,称得上是上美厂面向市场化制片收获的巨大成功。
而相当一部分的观众因为动画记住历经磨难、劈山救母的沉香,以至于沉香几乎取代了原本神话中“二郎神”的角色,成为公众心中“劈山救母”的唯一代言,也足见动画的社会影响。
在《我为歌狂》的制作中,上美厂更是全面拥抱市场。校园青春动画结合胡彦斌、灵感乐队、五彩精灵等歌手和乐队演奏的流行音乐,在当时幼儿向的国产动画中,显得独树一帜。而17岁的胡彦斌也凭借动画音乐大碟60万的销量,一跃成为青少年心中的一线流行歌手。
但在市场化带来的,更多是上美厂对新环境的水土不服。《宝莲灯》(1999)对比同期日本动画电影《幽灵公主》(1997)、《千与千寻》(2001)在作画、故事框架等方面已经呈现明显差距。而近似于幻灯片、大部分片段由静态图片表达的《我为歌狂》,也在作画、转场等重要环节上倍受舆论诟病。
《北京青年报》更是在2001年动画热播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刊文指出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我为歌狂》打出的旗号就是‘中国版《灌篮高手》’,它不仅学故事、学技法、学制作,更有一套完整的销售推广计划,借鉴日本以及美国动画片的经验。”

(当年的《我为歌狂》,随意一截就是“作画崩坏”)
但日本动漫的强烈冲击下,上美厂希望通过借鉴和学习所弥补的差距,显然不是仅仅模仿“画风”和“制作”方式就能完成的。而后面的时间线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为歌狂》大火之后,上美厂无力继续翻拍其小说的第二部《爱上爱情》,也没能再拿出具有影响力的新作品。接替中国动画制作的代表之一,是相继制作出西游记(1999)、哪吒传奇(2003)的央视青少年中心动画部,也就是后来的央视动画有限公司。
当然需要努力的也不仅仅只有制作者们。在行业环境层面,相关部分也相应出台过一系列激励措施,以鼓励优秀国漫的创作。比如2000年起,国家广电总局便对动画片引进和播放做出规定,“每天每套节目中,播放引进动画片的时间不得超过少儿节目总播放时间的25%,其中引进动画片不得超过动画片播放总量的40%。”
但客观政策带来的效果如何就见仁见智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如今口碑完成逆袭,以剧情堪称的《虹猫蓝兔七侠传》,也迎来过被高度怀疑为骗补助项目的《雷锋的故事》。
总之我们从时间线上看到的结果是,国人对中国动画低龄化的印象,随着电视屏幕上的卡通片不断加深。而人们不时翻出上美厂的影片,今夕两相比较,捶胸顿足,这种情绪最终变成了呼吁“国漫复兴”大基调。
徘徊和前路
从《铁扇公主》算起之后的80年里,“国漫”从启迪手冢治虫、影响宫崎骏,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高度美誉,到逐渐在历史进程中断层、掉队。与之毗邻的日本动漫产业,则逐渐拥有完整的生态和庞大的市场,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
这两个起点交织的产业线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是从何处走向分岔?1968年《周刊少年Jump》创刊,大概是这个分岔路上一个醒目的标志。
尽管此前已经有《周刊少年SUNDAY》和《周刊少年MAGAZINE》相继创刊,拿下各路漫画名家连载以及绝大部分市场,但《周刊少年JUMP》以颇为激进的新人招募,成功搅动市场,销量迅速攀升。
自1980年起,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作品,《龙珠》、《圣斗士星矢》、《阿拉蕾》、《足球小子》等作品接连从几家漫画周刊杂志中诞生。90年代末,《海贼王》、《棋魂》、《火影忍者》、《死神》等连载漫画不仅在日本享有超高人气,更是以各种形式、渠道影响走进中国。在文具盒、包装袋、书皮等等物品上,你都轻易可以找到路飞乔巴、鸣人佐助、柯南小哀等等角色形象的身影。
周刊杂志上连载的漫画,在几十年间为日本动漫产业持续输送强势IP,直到今天,漫改动画仍然是番剧的主流。根据网友nagatoyuc制作的2020年新番表来看,今年已确定的169部番剧中,有75部来自漫画改编,占比44.3%。对作者而言,漫画作品动画化是一种业界殊荣,而通过已经通过市场检验的漫画,也削弱了制作动画、开发周边、游戏等项目的风险。
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构建出一个日漫产业的理想模型:漫画家将作品投稿入杂志,获得良好的读者反馈,进而不断连载,并开始出版单行本。在这期间,受到投资公司制作人青睐,改编企划顺利通过,开始进入动画化。随着该IP不断收获粉丝,逐渐衍生出相应的周边产品或者游戏改编等二次开发。
套用这个模型,就不难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漫画一直存在缺位,相比于动画在上世纪60年的蓬勃、80年代的繁兴,漫画的高光更为滞后,更加短暂,甚至从未走进国漫产业的主线。
近代中国漫画的流行,大抵与近代报刊发展平行。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利用图画进行斗争宣传,成为近代漫画的主要内容。
1925年,《文学周报》以“子恺漫画”为标题,开始连续刊载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丰子恺的画作。也是那一年起,上海世界书局第一次使用连环图画作为正式名称,出版图书。进入30年代,画家叶浅予和张乐平陆续在报刊上连载《王先生》和《三毛流浪记》,反映时局下小人物的真实生活。
到了20世纪50年代,连环画进入空前发展,根据当时的数据显示,在连环画中心上海,有70余家出版书店,3000余处出售和出租书摊。等到了1985年,全国出版连环画达到3000种,印数达到8.16亿册,要知道当时的全国人口才刚过10亿。
可以说,连环画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拥有相当丰富的作画人才,而且拥有极大的读者市场。遭遇盛极而衰,乍一看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想也符合常理。
中国早期的漫画,似乎都在满足特定时代下功能性需求,即使是拥有精良的美术图画和文字故事的连环画,也承载着部分文化启迪的宣教职能,相较于更具娱乐属性的日漫来说,并不占优势。此外,连环图画趋于静态表达,而此时的日漫分镜则更具视觉冲击。而且从大环境上看,也缺乏进行动画化以及周边开发的产业条件。
用现在的话讲,连环画的读者黏性不强,变现渠道单一,行业天花板也很低。又恰好迎头撞上80、90年代日漫蓬勃的浪潮,也就遭受到了历史的选择。仅仅两年后,连环画种类减少58.7%,印数减少90.3%。
也有人尝试过扭转这一局面,1993年王庸声创办《画书大王》,在试刊号的发刊词中即明确提出了创刊的两大目的:一是“把我国新一代连环画作品奉献给读者”,二是“把世界上一流的连环画作品引进来和大家见面”。第5期上刊登了《漫画正名》一文,明确提出“本刊发表的连环画一律称为漫画”。
《画书大王》以及在“5155动画工程”中创立的《中国卡通》、《北京卡通》、《少年漫画》等一批杂志,为本土漫画开辟了一小块土壤,陈翔、颜开、郑旭升、赵佳、姚非拉、胡倩蓉、阿恒等青年漫画家,从这里走出来,开始被人们记住。但时至今天,这批杂志或是责令停刊、或是变卖刊号、或是在屡次改版中读者不断流失。一些初代漫画作者,逐渐隐退,还有的仍然留在业界,他们的粉丝刷着“爷青回”的留言,多少夹杂着对那个“黄金”时代的怀念。

(赵佳和《黑血》是本土漫画中绕不开的传奇)
在许多呼唤国漫崛起或者复兴的语境中,动画和漫画总是杂糅在一起。但在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当长远的时间轴上,中国动画和中国漫画的发展并没有太多交集。囿于历史发展和产业结构,漫画的市场关注和政策扶持,远不及动画。
这种长久的不平衡状态,在近十年来才开始改变的。
2006年创刊的《知音漫客》几乎以一己之力开拓彩漫市场,2009年有妖气拿下投资,开始转型为互联网漫画平台,2011年《十万个冷笑话》的走红,开始让人们注意到漫画改编的强大生命力。随着腾讯漫画、布卡漫画、快看漫画、漫漫漫画、网易漫画以及哔哩哔哩漫画入局。漫画在网络时代,被注入生机,动漫产业的生态也开始逐渐补课。
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人之下》、《狐妖小红娘》、《从前有座灵剑山》等动漫完成出海,《快把我哥带走》、《秦时明月》、《南烟斋笔录》等漫画被改编成真人电影电视剧。似乎在资本的青睐下,你画漫画我做动画,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我在旧书摊找到的《飒漫画》,也是同期的佼佼者)
不过也确实仅仅只能停留在“似乎”,因为新的模式也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并且相比于《我为歌狂》之于日漫,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太多“作业”可抄。
比如当大电影、真人电视剧成为动漫出圈标准时,摸索研制一套符合市场口味的题材和制作风格,就成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背后的隐忧则在于,奔着电影与电视剧而来的人群,是否会溯源到漫画动画,成为动漫产业中的消费者?
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至少从《陈情令》和《魔道祖师》来看,资本推动的出圈影响力对于漫画作品本身的反馈,难以被称之为“正向”。
另一个向度上,随着腾讯、B站、爱奇艺等平台对动漫产业的倾注,在为产业带来市场前景的同时,也将平台与内容的矛盾不断加剧。毕竟从网文行业身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当阅文集团已经成为绝对的规则制定者,写作者们在“55断更节”中表达的愤怒与无奈,已经显得太过微弱。
究竟国漫发展的未来,是形成独立成熟的产业体系,还是互联网巨头们泛娱乐版图中的一角。只能交给时间来检验了。
后记
在“崛而难起,复而不兴”循环里,被反复告知要宽容和等待的人们,如同拿着张破船票,紧了紧衣裳,踱着步子,在雾霭沉沉里等着迟迟未进港的国漫巨轮。就算不能知道等待的终点在哪里,再不济也要在港口生一团火,持续添柴,暖人心。
我还记得去年10月,我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提问“儿子都19岁读大一了,为什么还喜欢看动画片?”
一年多来,该问题累计浏览量超过846万,引发的关注,虽然不及“如何评价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逾2000万的浏览量,但数据已经达到“如何评价《罗小黑战记》动画电影?”的四倍。截至11月4日,共获得5592个回答,甚至连A站官方号都亲自“下场”。
其中大多数的回答围绕“动画是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展开讨论,但事实上,看动画等同于幼稚,这一刻板印象由来已久,相当一部分网友都表示,不仅是自己的家长,甚至一些朋友也存在这种偏见。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争议,不仅仅是家庭矛盾,父辈与孩子的代际冲突,更大范围来说,它可能是泛二次元用户所承受的群体偏见的一角。
而想要暖人心的火和柴,大概就是国漫从业者有着相对可观的收入维持生计,漫画家安心版权的归属,自由创作,当年轻的孩子告诉父母和同学,自己未来要画漫画、做动画时,不会被当做一个不正经的梦想。
上一篇:互联网巨头放贷的AB面

 2020-11-12 15:30:13
2020-11-12 15: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