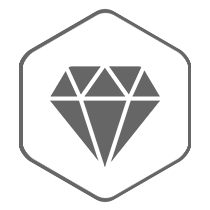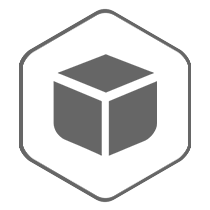《异形》中的抱脸虫利用了人类历史上民间传说和宗教中具有象征性的恐惧意象
《异形》中的抱脸虫利用了人类历史上民间传说和宗教中具有象征性的恐惧意象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从本质上来说,异形是一种丑陋的、令人厌恶的、由蜘蛛和蛇等动物混合而成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把对这种外星掠食者的恐惧理解为,这只不过是好莱坞制造出来的肤浅的恐怖效果。但实际上,这种恐惧也揭示了人类认知和文化演化中的重要事实。我们天生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而这些情绪具有适应优势。《异形》的抱脸虫让我感到动弹不得的恐惧,这可能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接触蛇和蜘蛛的经验遗存。此外,异形所具有混合特征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人类的历史。
混搭的怪物
似乎每种文化的民间传说和宗教中都有可怕的混搭怪物。它们出现在人类最早的文献中,也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中。埃及吉萨的狮身人面像,即半人半狮的怪物斯芬克斯(Sphinx),至少有4500年的历史。在《吉尔伽美什史诗》(公元前2100年)中,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和恩奇都(Enkidu)与一个名叫胡姆巴巴(Humbaba)的混血怪物展开战斗。印度教的毗湿奴(Vishnu),在一些印度文献中的形象是凶猛的狮头人身怪物,名为那罗希摩。湿婆之子葛内舍(Ganesha),是一个长着象头的类人生物,又被称为象头神。古希腊神话中有许多混合的奇幻生物,包括半人马、萨堤尔(半人半羊)、美人鱼、帕伽索斯(长着双翼的马)、九头蛇、狮鹫、奇美拉(上半身像狮子,中间像山羊,下半身像毒蛇)等等,不断地在好莱坞的电影中复活。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从《贝奥武夫》到托尔金,再到J。 K。 罗琳,文学作品中展现了无数的合成生物和变形形象。近年来,我们又时常见到人类和机器的结合。
 摩蹉(Matsya)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十个化身中的第一种,通常形象为上身为人,下身为鱼
摩蹉(Matsya)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十个化身中的第一种,通常形象为上身为人,下身为鱼那么,为什么要把生物分类打乱,再进行整合呢?心理学家丹·斯佩伯(Dan Sperber)和人类学家帕斯卡·博耶尔(Pascal Boyer)认为,人类对世间万物有一种天生的,或者说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民间分类法。我们会想办法将世界组织成各种可预测的分类,以便于理解、认知和操作。甚至当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有能力把人、鸟、虫子、树和鱼各自归类,它们在自己的类别中很相似,但与其他类别又很不同。小孩子经常把鲸看成“鱼”,而早期的自然史也犯了这个错误。对鲸的民间分类揭示了人们自然分类的简单性;如果一个动物能在水里游泳,看起来像一条鱼,那它就是一条鱼。不过,我们前科学时代的祖先并不需要对鲸有更细致入微的了解,他们的认知只需要满足生存所需就够了。
大多数人心中似乎都有非常宽泛的分类学概念,比如“动物”、“无生命物体”,但也有进一步的区分,比如“爬行动物”、“飞行动物”和“四条腿的动物”等。不管这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的大脑在处理日常经验时都会用到这些心理类别。大脑利用这些类别来分析各种杂乱而困惑的感官信息。我们称之为“认知的预测加工理论”,强调了大脑的模式识别系统。我们的大脑创建了对世界万物的预测模型,帮助我们从周围的信息噪声中提取有用的信号。
具有黏性的模因
违反这些类别的事物会强烈地唤起人的意识。毗湿奴拥有数十条手臂,神话中的蛇会像龙一样飞行,当这些形象打破我们对事物的预期——“人只有两条手臂”、“蛇不会飞”——时,它们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并在认知上变得富有“黏性”。它们牢牢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很容易被回忆起来,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迅速传播。换句话说,杂合怪物是优秀的模因(meme)。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首先提出了模因的概念,指出模因作为文化片段或认知单元,具有与基因相似的特征,能够在无需有意识的设计或目的的情况下,在人群中广泛传播,。非自然的想法或图像之所以能够保存并传播,是因为它们让我们感到惊奇,使我们更难忘记或忽视它们。
 杂合怪物是优秀的模因,它们牢牢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很容易被回忆起来,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快速传播
杂合怪物是优秀的模因,它们牢牢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很容易被回忆起来,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快速传播人类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认为,杂合怪物之所以在青铜时代大量产生,是因为新的贸易路线和文化融合引发了心理焦虑。通过创造怪物,可以将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恐惧转化为具体形态,以及令人厌恶和恐惧的对象。
怪物看起来不大像有益的模因,因为它们会吓到我们,增加压力,但它们几乎一直是更宏大的警世故事文化的一部分。在道德规范的执行中,怪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你不遵守规则,怪物就会来抓你;如果你不行美德,魔鬼就会把你带走;如果你暴饮暴食,你下辈子就会变成“饿鬼”(根据佛教传统)。大多数怪物的功能是作为令人厌恶的威胁,被英雄和神明征服、否定,并清除出人间社会。它们为真实的社会(我们)如何抵抗真实的敌人(他们)提供了“排练”。怪物是具有黏性的模因,能将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形成道德共同体。
这也意味着,奇幻传说有助于文化本身一些核心元素的形成,因为怪物和英雄通过文化亲缘关系营造了社会的团结。奇幻的反事实性是创造文化亲缘关系的最早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早期人类群体发展到超越遗传亲缘关系的社会规模,文化参与了虚构的亲属群体的形成。非亲非故的人感觉就像兄弟,能有效地合作,共享资源,为彼此杀戮和死亡。虚构的亲属群体不会因抽象或理性的伦理原则聚在一起,而是在毗湿奴、耶稣、孙悟空或万物有灵论的仪式和教派的周围集结。换句话说,他们会聚集在杂合怪物和其他“黏性”模因的周围。
类别错配与普遍情感
长期以来,杂合怪物的故事一直与宗教的进化密不可分。宗教起源于像民间分类学这样的前认知(或前适应)。如果民间分类将世界划分为可预测的模式,那么偶尔的类别不匹配就会引发独特的认知唤起,产生超自然主义。会说话的人工制品,或者复活的已死生物,都属于相对简单的类别转换。我们大脑的预测模式因此混淆,而同个类别的混搭则产生了恐怖的生物。
然而,类别错配理论往往忽略了情感因素。仅仅假设认知类别的颠覆会突然产生一个超自然实体是不够的。例如,我们头脑中存在一个狗的概念,但是想象一只有三个头的狗并不会产生像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守卫冥界的地狱三头犬)那样的可怕影响。认知类别的内容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情感基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物体、动物和人都会引发低层次的“接近”或“回避”情绪,但“滑行者”(slitherers)或“爬行者”(crawlers)这类词在情绪方面的影响尤其强烈。
当我们概念化神或怪物或其他模因时,这些概念就被注入了恐惧、欲望或愤怒的色彩。情感联系是将世间万物分为“危险”和“有益”两大类别的最古老形式。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共享这个早期的分类系统。
情感联系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间分类。虽然类别不匹配会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并提高记忆持久性,但带有强烈情感关联(比如蜘蛛恐惧症)的杂合动物尤其具有“黏性”。有效的恐惧(和宗教)已经找到了能无意识地触发我们原始情感的符号和故事。正如文化理论家马蒂亚斯•克拉森(Mathias Clasen)在《为什么恐怖很诱人》(Why Horror Seduces)一书中所指出的,类似的怪物和恐怖故事能在有着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起作用。恐怖具有普遍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普遍受到民间分类类别的支配。因此,在世界各地,任何人都会感受到恐怖怪物的“魅力”。但更重要的是,人类具有通用的情感系统,能将对自然掠食者的恐惧与文化意象联系起来。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具有诸如战斗或逃跑这样的适应本能,但这些都是旧的大脑系统,主要存在于脑干中。大脑的情感回路(包括杏仁核、下丘脑和海马等边缘区域)与本能的运动系统,以及更高的认知能力交织在一起。已故的神经学家、情感和哺乳动物研究的先驱雅克·潘斯基普(Jaak Panskepp)确定了哺乳动物共有的7种主要情感系统:恐惧、关心、欲望、愤怒、恐慌、寻觅和玩耍。每一种神经回路都有其独特的通路穿过大脑,产生特定的神经递质和激素,并导致特定的哺乳动物行为。例如,恐惧有一种神经回路,它从杏仁核经过下丘脑到达脑干,再传递到脊髓。
原始的恐惧遗存
和其他生物特征一样,恐惧也受演化的影响。达尔文多次把蛇(既有真的也有假的)带到伦敦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馆。他发现,黑猩猩对蛇有着极度的恐惧。他开始思考黑猩猩这种对有威胁物种的有益恐惧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蛇的经验信息又是如何储存在灵长类动物的DNA中,并一直传递下来?
类别错配假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恐惧来自认知或分类的混乱,而不是来自认知的内容。情感唤起来自于认知混乱,而不是动物或怪物本身。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混乱都会让观众产生恐惧。我们不害怕迪士尼的芭蕾舞河马或托马斯蒸汽火车头。此外,像恐惧这样的情绪似乎与某些环境威胁有关,而恐惧的到来,要比单纯的分类混乱更快、更有力。
一种情况可能是,人类对爬行动物的恐惧从来都不是通过条件学习、观察或经验“习得”的。具有随机恐惧反应和蜘蛛感知能力的原始人类,要比具有随机恐惧反应和树木感知能力的原始人类繁殖得更好。恐惧会让你逃跑,而逃离毒蜘蛛比逃离无害的树木更有适应优势。在这种观点下,所有人类都继承了一个突触编码,不依赖于“学习”(观察有毒蜘蛛的危害),而是机械地用恐惧来描绘对蜘蛛形状的感知。如果大脑产生了一种看到蜘蛛形状就分泌肾上腺素的预测模式,那么我们就能远离毒蜘蛛,具有足够长的寿命来复制这种模式。
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和沃尔夫冈·施莱特(Wolfgang Schleidt)分别对动物的恐惧进行了实验,发现这并不是对特定捕食者的固有恐惧,而是一种发育过程中认知类别和情感的配对。当鸟类和哺乳动物出生时,它们有灵活的类别来存储各种关联。但这些类别在出生后会迅速固化,成为解读其他事物的默认方式。当任何奇怪的生物(与默认类别不对应的生物)出现时,动物就会变得兴奋和恐惧。通过让鸣禽在早期接触鹰的形状(鹰是自然捕食者),研究人员消除了它们对鹰的恐惧;但如果在晚期接触鹅的形状(鹅对它们没有威胁),则会让鸣禽产生恐惧反应。
根据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的“奇怪情境”实验,人类的默认类别在6个月左右就会固化,而6个月以后的婴儿会对任何“奇怪的事情”感到害怕。如果人类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绑在母亲身上,或者被其他方式保护着(而且不接触地面),那么一旦遇到各种各样在地上爬行的动物,就会从根本上打乱孩子出生后六个月的默认分类。
这项研究涉及人类认知和情感的发展,解释了人类普遍具有的恐惧症(包括蜘蛛恐惧症、爬虫恐惧症、黑夜恐惧症、幽闭恐惧症和深水恐惧症等)相对较少的原因。一旦文化开始将这些元素融合到宗教和恐怖故事中,这些意象就会变成极具黏性的模因。
难怪《异形》里那个抱脸虫会让我感到恐惧,至今依然如此。它不仅激发了原始的大脑过程,而且还把我和我的文化遗产,以及我所属的物种联系在一起。遵循早期的宗教和文学传统,好莱坞的恐怖电影在不知不觉中,开发了同样深厚的生物文化宝库。(任天)

 2019-10-08
2019-10-08